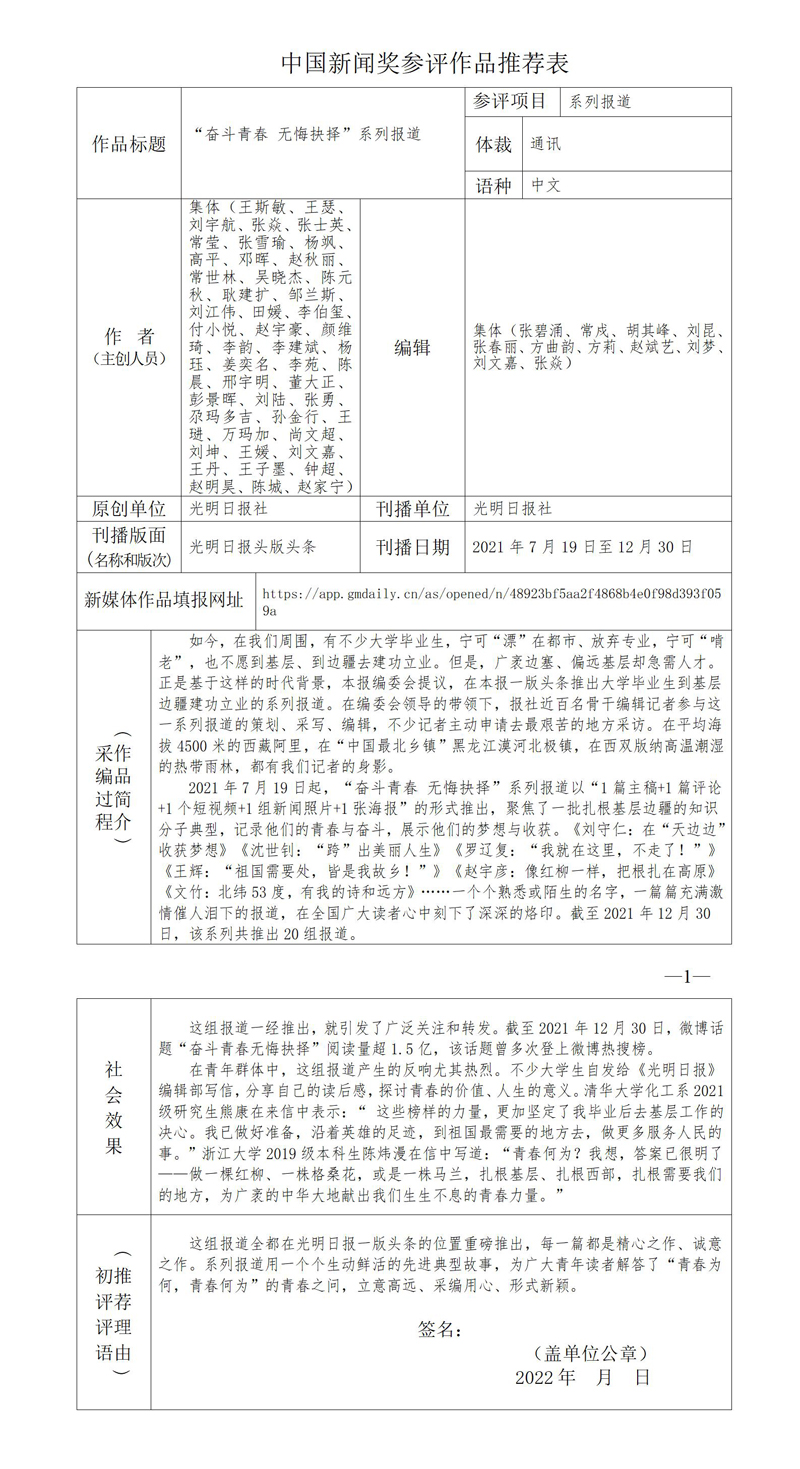 cription="编辑提供的本地文件" sourcename="本地文件"/>
cription="编辑提供的本地文件" sourcename="本地文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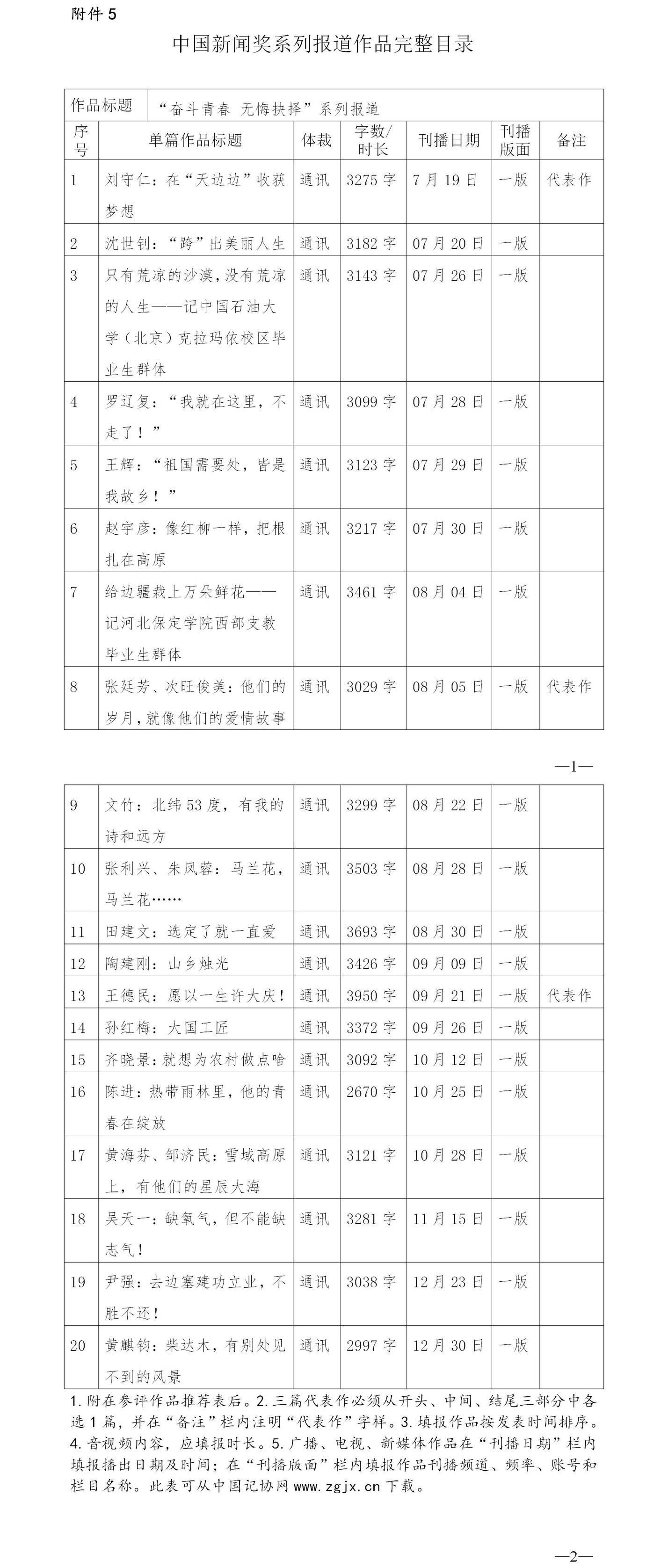 cription="编辑提供的本地文件" sourcename="本地文件"/>
cription="编辑提供的本地文件" sourcename="本地文件"/>

 cription="编辑提供的本地文件" sourcename="本地文件"/>
cription="编辑提供的本地文件" sourcename="本地文件"/>
刘守仁:在“天边边”收获梦想
2021-07-19光明日报头版头条
本报记者 王斯敏 王瑟 刘宇航 本报通讯员 吴存远
6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名誉院长刘守仁的名字出现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名单里。
此时,87岁的老人正病卧于新疆石河子一间医院病房内。11天前,他在病床上戴上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位人称“军垦细毛羊之父”的绵羊育种学家,迄今光荣在党59年,扎根边疆66年。
大学毕业,他在分配志愿书上写下“去最艰苦的地方,干最艰苦的工作”,提着两箱书奔赴边疆。他用毕生心血,使我国拥有了高品质细毛羊,结束了中国高档羊毛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也用伟岸人生,回答了一道关于轻与重、苦与甘、个人与国家、付出与收获的选择题。
“把阿尔泰羊的皮毛披在哈萨克羊身上”
1955年11月,天山北麓,石河子紫泥泉种羊场。一辆大卡车裹着尘土缓缓停下,一位青年“蹭”地跳了下来。
单薄的身形,不高的个头,瘦长脸上一双闪亮的眼睛。这是21岁的刘守仁。几个月前,他从母校南京农学院出发,颠簸数十天到了乌鲁木齐,又执意从被分配任教的八一农学院调到这个深山牧场。
刘守仁大学报考畜牧专业,是因向往父亲友人描画的壮丽图景:“社会主义煤炭工业大发展,需要马车运输。一边是机器轰鸣,一边是万马奔腾”;毕业奔赴母亲眼里的“天边边”,耳畔响着的是父亲的勉励:“大城市有舒适的生活,但草多、牲畜多的边疆,才是你建功立业的地方。”
一切从国家需要出发,让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尽快强起来!生于江苏靖江,从小亲历家乡沦陷之痛、被迫辍学三年的刘守仁,深知“国强方能民安”的道理。
辗转到达第三天,他被任命为技术员。
“当时种羊场只有哈萨克土种羊,毛粗色杂,只能用来做毛毡。而新中国毛纺工业正起步,急需细羊毛。”看着从苏联引进的几只阿尔泰细毛羊,刘守仁动了念头:能不能杂交改良,把阿尔泰羊的皮毛披在哈萨克羊身上?
一场瞄准世界前沿的“长跑”开始了。
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皮鞭学放羊,熟悉绵羊习性。哈萨克族牧民们惊奇地发现,曾被他们认定很快会被苦日子吓跑的“知识客”,竟变成了追着羊群漫山跑的“好把式”。不到6个月,他就出了师,单独放起有360只母羊的试验羊群。
没有实验室,他搜罗来大大小小的空瓶子做容器,自制各种简易工具。最基本的工作——数羊毛测品质,因为没有密度钳、烘箱和天平而成了难事。他自有“笨办法”:用竹片做成一平方厘米的格子扣在羊身上,剪下格子里的毛,拿小镊子一根一根数。每只羊至少得取样四处,每个小格子的羊毛都在5000~10000根,常常数得眼睛酸痛、泪水长流。
最大的考验莫过于接生羊羔。20天内,300多只母羊集中产羔,土棚子里成了血水、胎衣、羊粪的世界,腥膻恶臭。他给羊羔剪脐带、编号码、称体重,给母羊喂水喂食,忙得脚不沾地。
为了让羊群吃得更好,他收集研究牧草170多种,还在天山深处跋涉7天,几次险些从冰达坂上跌落,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花牛沟草场……
几年下来,刘守仁调查整理了6万多个数据,理清了阿尔泰羊的五代谱系,做了数不清多少次杂交实验。
比起“细毛羊之父”,更愿意听人叫他“天山之子”
收获的季节到了。
1957年春日,第一只毛细如丝的杂交羊羔降生在紫泥泉。老牧工们记得,那一刻,刘技术员像看到了自己的尕娃娃,扑过去把羊羔子搂起来,捧到被窝里,用洗脸毛巾把羊身上的胎衣、血水细细擦干净。疼爱得了不得!
刘守仁既喜悦又清醒。根据国际经验,培育一个成熟新品种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果然,第一批杂交羊羔毛色变杂,出现“返祖”现象;第二批杂交羊羔近四成不幸夭折……一点点摸索,一关关攻克。1965年,杂交羊羔成活率提升至98%;1968年,细毛羊亮相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不久后,农垦部正式将其命名为“军垦细毛羊”。十多年冲刺,梦寐以求的新品种诞生了!
刘守仁很快有了新目标。这次,“要把国际顶级的澳洲美利奴羊的皮毛披在军垦细毛羊身上”。
又是15个春秋。1985年,中国美利奴羊(新疆军垦型)通过国家鉴定,达到国际优质毛纺原料水平。
就这样,刘守仁团队持续育得2个新品种、9个新品系,推广至全国25个省区市,创造经济效益50多亿元。
荣誉也纷至沓来。从全国科学大会受表彰,到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从全国人大代表,到中国工程院院士。边疆热土不曾忘记这位赤子砸下的每一滴汗珠。
而他最感念的,是那些平凡牧工们。
紫泥泉种羊场深处,立着一座石碑,上书“牧羊人陵园”。这是刘守仁出资竖立的。陵园内长眠着多位牧工,每逢清明节,他都会来这里坐一坐。
“他们都是我的老师,细毛羊的功臣。”刘守仁总是念叨着这样一串名字——
肖发祥,脑中装着一部牧羊百科全书,视羊如命。有重点种羊、病羊,刘守仁都放心交给他。
哈赛因,快乐的哈萨克族“天山通”。遇到羊羔病亡率高等烦心事,找他请教,总能得到朴实管用的答案。
…………
这些牧工教给刘守仁难忘的道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不论干出多大事,在人民面前永远是个小学生。
刘守仁喜爱草原、松林,喜欢壮美的天山。比起“细毛羊之父”,他更愿意听人叫他“天山之子”。
“他的整个人和心,都‘种’在这里了。”现任紫泥泉种羊场场长的何其宏感慨。
像一面旗,在边疆凝聚起“现象级团队”
1989年,刘守仁调任新疆农垦科学院院长。上任之初,全院没有一个博士。想办法引才,却留不住。那就自己培养!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刘守仁开始在南京大学、石河子大学等院校带博士。
“为了让我们尽快打开科研视野,老师多方联络,送博士们去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型实验室学习,或与当地导师联合培养。”新疆农垦科学院副院长周平告诉记者。
2000年,从四川来院里工作两年后,周平被送往内蒙古大学旭日干院士处,在其带领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硕博连读了6年。学成之际,何去何从?周平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到了刘守仁身边。“想想他对新疆的执着,再看看他对我们的一片苦心,怎可能不回来。”
刘守仁的执着,是一面高扬在学生们心中的旗帜。
早在1978年,浙江、南京便有高校力邀刘守仁去执教。常年在家乡居住的妻子、两个儿子喜不自胜。然而,他谢绝了:“一个科学家,离开事业就失去了价值。细毛羊在新疆,我就在新疆。”
在刘守仁的感召下,一个“现象级团队”出现了:十几位从大城市深造回来的博士凝聚在新疆农垦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酝酿着新的突破。2016年,以刘守仁为首席科学家的省部共建绵羊遗传改良与健康养殖国家重点实验室落户该院,更是给了这个团队无尽力量。
几乎每个人,都有深藏心底的感动故事。
甘尚权研究员记得,刘院士曾“得意”地对年轻人说:“光看羊尾巴,我就知道是哪只母羊的崽。”他要求大家都俯下身和羊接触,“光在实验室里搞分子、搞DNA,连羊都不认识,怎么行?”
王新华研究员任院长期间,刘守仁常督促他:你晚上来院里看了吗,咱们实验室的灯亮到几点?“同样的话,他在全院大会上也讲过,意思是提醒年轻人珍惜青春,在工作上多下功夫。而他自己,多少年一直这样做。”
今天,抱病的老人仍牵挂着他的羊。顺应国家发展需求,他们的团队一面继续攻关超细型细毛羊新品系,一面在多胎肉羊、肉用羊“新疆白”的选育上持续探索。
每次大家去探病,只要谈起羊,刘守仁脸上便焕发神采。石国庆研究员说,老师一定又想起了他总提起的那个梦:蓝天上、绿草间,一朵朵“白云”飘啊飘。那不是云,是我们的细毛羊,飘出一望无尽的美好希望,汇成最为动人的华彩乐章……
 cription="编辑提供的本地文件" sourcename="本地文件"/>
cription="编辑提供的本地文件" sourcename="本地文件"/>
张廷芳、次旺俊美:他们的岁月,就像他们的爱情故事
2021-08-05光明日报头版头条
本报记者 刘江伟 光明网记者 田媛 李伯玺
列车在天路上飞驰。翻过唐古拉山,海拔渐渐走低,一片茫茫的大草原迎面而来——进西藏了!
2020年9月,受央视《国家宝藏》节目组之邀,74岁的张廷芳重走当年的进藏路。看着车窗外熟悉而久违的风景,往事如潮水般涌来,她的眼中泛起泪花。
40多年前,张廷芳和次旺俊美来到西藏,并肩走过艰苦岁月,共同筹建西藏大学。他是首任校长,她做过副校长。而今,她的次旺俊美离开快六年了。
在车上,有人问张廷芳:“当初为啥不远万里赴藏?”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因为爱情!”
“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究竟是什么样的爱情故事,让张廷芳对西藏如此眷恋?在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记者走进了她在北京的寓所。
眼前的张廷芳,满头华发,目光炯炯有神。聊起次旺俊美,她言语间透着深情:“大学时,次旺俊美个子高高的,普通话好,会唱歌,会跳舞,会弹扬琴,还会拉二胡。”
记忆的闸门打开,往事汩汩而出。
1965年,北京姑娘张廷芳和西藏小伙次旺俊美同时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她在中文系,他在教育系。在学校宣传队,他们常常一起排演节目,去工厂和乡村演出,空闲时聊爱好、聊人生、聊理想,展望未来的生活。两个年轻人志趣相投,渐渐相恋。
美好的时光,在毕业时停住了脚步。次旺俊美是北师大招的第一个藏族本科生,一门心思回家当老师。张廷芳犯了难:跟着去西藏,还是留北京?她爱次旺俊美,想去西藏,“如果因为我,他没回西藏,他的藏文就荒废了”。
但,从北京到拉萨,远隔千山万水,光路上就要十几天。况且,母亲常年多病,弟弟尚未成年。她走了,家里怎么办?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张廷芳犹豫不定。她决定跟父亲深谈一次。
父亲是老党员,支持她去国家更需要的地方,到西藏实现理想。为此,他还做通了家人的工作。
1971年12月,在北师大的一间教室里,张廷芳和次旺俊美举办了婚礼。在新婚的甜蜜中,他们边等毕业分配计划,边筹划即将到来的西藏之行。
结果却出乎意料——毕业分配方案中,压根没有西藏!
怎么办?西藏更需要他们,更适合次旺俊美。他们毫不迟疑,向学校递交了自愿去西藏的申请。
如愿以偿。1972年夏天,张廷芳夫妇终于坐上了西去的列车。“我不知道前面等我的是什么,但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张廷芳有股拗劲儿。
“西去列车这几个不能成眠的夜晚呵/我已经听了很久、看了很久、想了很久/我不能,我不能抑制我眼中的热泪啊/我怎能,怎能平息激跳的心头?!”20世纪60年代著名诗人贺敬之的诗《西去列车的窗口》,曾激励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奔赴西北。此时,这首诗又陪伴他们进藏。
先坐火车到西宁,然后坐汽车沿青藏公路一路向西,他们走走停停半个月,才抵达拉萨。
布达拉宫近了!司机把车停在路边,让他们下来洗洗脸。张廷芳走出车门,顿时被震撼了:蓝的天,绿的树,白的羊,青的草,远处静默矗立的雪山,眼前湍流而过的溪水——西藏原来如此美丽!
“我们的生命已深深融入这所大学和她置身的土地”
在张廷芳北京的寓所中,摆着一幅他们初入藏时的照片——一间不大的房子里,装满了书,张廷芳夫妇围坐小书桌,认真地看书。看不出紧张和忙乱,只有两人时光的浪漫与静好。
“表面平静无事,内心江海翻滚。”张廷芳笑着对记者说。
那时,张廷芳夫妇被分配到西藏师范学校,她在汉语教研组,他在藏文教研组。教学条件极其简陋,教室和宿舍都是铁皮屋顶,低矮阴暗;晚上没有电,蜡烛也供应不上。生活的困难可以克服,但语言不通是大问题。
第一次上课,张廷芳就泄了气。学生们两眼直直地盯着她,没有任何反应。怎么回事?教得不好吗?她赶快求助教研组长。教研组长问了学生,回到教研室,哈哈大笑:“小张,你知道学生怎么说你?这个普姆(姑娘)说话真好听,像中央台广播员,可我们什么都不懂。”张廷芳痴痴站着,笑不出来。
次旺俊美鼓励她,用汉语讲课不能改,但可以用少量藏语辅助。他在张廷芳备课的生词表下面,逐个注上藏文。张廷芳上课时,连画图带比画,学生们才大概其明白。后来,为方便学生们学习,她和次旺俊美一同编了一套汉文、汉语拼音、藏文三对照的《汉语文》教材,很受师生喜欢,还流传到拉萨之外的地区。
有爱人的陪伴,艰难的日子有了很多生趣。张廷芳怀孕后,特别想吃水果。这可难坏了次旺俊美。他满大街地找,连一个水果摊都没有。有一天,他兴高采烈地跑回来,满头大汗地说:“廷芳,我买到水果啦。”张廷芳看后,真是哭笑不得,三个核桃大小的青苹果,又苦又涩,根本没法吃。
1983年,中央决定以张廷芳夫妇所在的学校为基础,筹建西藏大学,次旺俊美被任命为筹备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这是青藏高原上第一所综合性大学,筹备任务极其艰巨。
这可忙坏了次旺俊美。写请示、打报告、搞调研、找经费,忙得团团转。两人白天见不到面,便相互留条子:“我有事不要等我”“饭给你放锅里了,中午热了吃”……不到一年,次旺俊美瘦了20多斤,颧骨高高凸起,像两座小山丘。
1985年7月20日,西藏大学正式成立,西藏高等教育翻开崭新一页。次旺俊美被任命为首任校长,张廷芳担任语文系副主任。
回首在藏大的日日夜夜,张廷芳感触很深:“我们和西藏大学走过了创建、摸索、发展的岁月。经过半生建设,我们的生命已深深融入这所大学和她置身的土地。”
“我的爱人陪伴我成长,西藏成全了我的人生”
张廷芳和次旺俊美一直有个念想,等有时间了,一起出去转转,就他们两人,看看北京胡同,探访援藏战友……但是,工作一桩接着一桩,似乎没有尽头。
1992年,次旺俊美来到位于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担任院长,夫妻分居了六年。1998年,次旺俊美调回西藏,担任西藏社科院院长,张廷芳被任命为西藏大学副校长。2006年,他们同时退休。还没回过神儿,又一项重大任务找到了次旺俊美——我国启动西藏梵文贝叶经保护和研究工作,次旺俊美被任命为自治区贝叶经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次旺俊美一头扎进工作中。他带领7人课题组,踏遍西藏41个县的寺庙、遗址,不放过一片贝叶甚至残片。历时6年7个月,他们共整理出西藏贝叶经1000多函(种)、近6万叶,取得了8项阶段性成果。
2013年秋,贝叶经工作告一段落,次旺俊美和张廷芳松了口气,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
谁料命运当头一棒——2014年年初,次旺俊美被确诊癌症晚期。不到八个月,他就离开了人世。
“次旺俊美就是为干事业而生的。作为国家培养的知识分子,他始终牵挂着工作,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说到这里,张廷芳扭过头,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
“我当初做了非常正确的决定,选择了次旺,选择了西藏。我的爱人陪伴我成长,西藏成全了我的人生。”采访结束,张廷芳拿出一本杂志,翻到折角处,那是次旺俊美发表的诗,就像他们的爱情故事——
“姑娘动人的羌协(即酒歌)引来白亮的圆月,/人们高举银杯扬起青稞酒的芳香,/祝福,憧憬,爱情……/生活的脉搏在雪山环抱的乡村跳荡。”
 cription="编辑提供的本地文件" sourcename="本地文件"/>
cription="编辑提供的本地文件" sourcename="本地文件"/> cription="编辑提供的本地文件" sourcename="本地文件"/>
cription="编辑提供的本地文件" sourcename="本地文件"/>


王德民:愿以一生许大庆!
2021-09-21光明日报头版头条
本报记者 王斯敏 张士英 李苑 邹兰斯
他是我国石油开采专业首位工程院院士,院士登记表里这样评价他的工作:“这些工艺,都是世界上油田开发意义重大、难度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技术”。
国际小行星中心将210231号小行星命名为“王德民星”,命名公报中如是介绍他的身份:中国油田分层开采和化学驱油技术奠基人。
见到84岁的王德民院士时,他刚动过腿部手术不久,步履还有些迟缓。
“不影响工作!”问起手术,他满不在乎,身姿依然笔挺。
“荣誉只代表过去!”说起成绩,他轻描淡写,面庞清癯冷峻。
唯有和记者聊起石油,他才滔滔不绝,眉宇间渐渐透出一股俊朗少年之气。自从23岁来到大庆,他始终在和石油“过招较劲”,也不曾忘记当年立下的誓言:“到大会战前线去,为国家拿下大油田!”
“那时常说‘百废待兴’,这些都是最‘待兴’的”
1960年隆冬,松嫩平原滴水成冰。王德民和几位工人扛着100多公斤重的绞车,从一口油井挪向另一口。
他们要用绞车把测试仪器送到井下。可严寒中井口冻死,仪器下不去。
怎么办?王德民和工人们解开棉袄包住井口,又把冰冷的防喷管抱在怀里焐热。等原油化开,仪器下井,嘴唇早已冻紫了。
此时,他刚到大庆4个多月。
中瑞混血的王德民,生于河北唐山,后举家迁至北京。自小家境优渥,父亲曾任同仁医院副院长,母亲在高校执教。出生5个月,日寇发动“七七事变”。童年时期,战乱成为他最深痛的记忆,“国家不强大就会被欺凌”的意识,也深深印在他幼小的心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王德民升入汇文中学读初中。高二那年,学校组建以新中国兵器工业开拓者吴运铎命名的“吴运铎班”,品学兼优的他成为其中一员。
第一次听吴运铎来校作报告,他深受震撼。
“题目是《把一切献给党》,讲了7小时。我和同学们泪流满面。”王德民把这位“中国保尔·柯察金”的事迹重温了一遍又一遍,一个信念刻在心中:“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祖国献出一切!”
1955年高考后,甲等生王德民挥笔写下七八个志愿,专业几乎全是石油、水利、钢铁之类。原因很简单——“那时常说‘百废待兴’,而这些都是最‘待兴’的”。
北京石油学院录取了他。当时中国石油极缺,老百姓把汽车用的汽油、点灯用的煤油都称为“洋油”。西方专家有关“中国贫油”的论断,像山一样压在中国人头上。
五年大学生涯,王德民学到了许多采油科技知识。大三实习,还参加了川中石油会战。“结果让人失望。国家寄予很大期望,但这里很快不出油了。”他说,“我切身体会到,搞石油太难!但越难,越需要有人做,越要靠科学。”
毕业前夕,石破天惊的喜讯不期而来:中国最大的油田——大庆油田横空出世,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开展石油大会战,新中国将“贫油国”的帽子一举甩进太平洋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石油学子们欣喜若狂,“大家敲脸盆、唱着歌,喧腾了一整夜”。紧接着,王德民的同学中有一批被派往大庆。随后,振奋人心的消息不断传来:大庆是一片“奋斗的热火”,汇聚了王进喜等一大批舍身奋战的“铁人”,他们用最短的时间打出一口口新的油井……
王德民激动难抑。终于等到毕业,他放弃留校机会,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大庆:“搞石油不去油田,何谈报效祖国!”
“大庆等不得,我也不怕那么多了”
王德民工作后的第一个职务,是油田地质室测压组实习员。
时值大庆“测压会战”,目的是弄清数百口生产井的地层压力。然而,国际通行的测压法“赫诺法”并不适用,测压偏差很大。
中国得有自己的测压法!王德民发起攻关。
白天工作到晚上七八点,刨两口饭就开始自学热传导数学、水力学、俄文,直到凌晨两三点;夜里穿越大片苞谷地去图书室借书,被敲门声惊醒的图书管理员好心提醒他:这片地界晚上有狼……
几个月过去,王德民系统掌握了国外各种测压法,无数次推演隐隐有了答案。
1961年2月14日,除夕夜。油田发给每人半斤白面、一碗肉馅,让大家包饺子。
喜气洋洋的职工食堂里,王德民看着手里的面粉和肉馅,皱起了眉头。
“这不得把大半天‘包’进去?不行!可我也饿啊。”灵机一动,他把面粉擀成两张“大饼”,捏了两个特大号“饺子”,煮了半小时,便不顾生熟捞起来吃下肚去,回到宿舍继续奋笔疾书。
灵感,在辞旧迎新之夜冲破最后一道屏障。王德民推导出了中国第一套、世界第三套不稳定试井测压公式!从此,被命名为“松辽法”的公式在全油田应用,精度比“赫诺法”提高两倍。
其后十余年,王德民接连研制出多层试油、油水井分层测试等工艺,助力大庆油田二次采油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他的过人胆识,也为人们津津乐道——
用直径2.2毫米的钢丝替代大型通井机,实现了测试仪器钢丝化投捞,既经济,又灵便。
研发偏心配产、配水器,解决了同心配产器“取一层须拆所有层”的弊病,配水合格率提高40多个百分点……
“特殊年代,每次请战都冒着‘白专’风险。何况,我还有外国血统。”王德民感慨,“但大庆等不得,我也不怕那么多了。”
“相当于又找到了一个大油田”
春潮澎湃,改革开放大幕拉开。此时,大庆油田已保持10年稳产高产。
怎样再稳产10年甚至更久?必须开发新储量。
新储量是有,但开采难度极大——与国外油田一般只有几个油层不同,大庆油田油层少则80多个,多则140多个,其中1/4是0.2~0.5米的薄油层,国际尚无开采先例。
“中国人来开这个先例!”又是一番夜以继日。两年后,王德民牵头研制出“限流压裂法”,可一次压开20~30个乃至70个薄油层,使低渗透层变成了可经济开采的油层。大庆油田地质储量猛增7亿吨,“相当于又找到了一个大油田!”
王德民并不满足。此时的大庆,采收率40%,已到水驱的极限值。他把目光投向世界性难题——化学驱三次采油。
很多人劝他慎重,因为国外权威早已断言:三次采油是“未来技术”,目前无法实现。
“不干怎么知道呢?就要在‘没希望’的地方找突破。”王德民研究了美国应用化学驱失败的大量案例,列出8大类、200多项课题,形成了周密的试验思路。
方案终获批准。十年艰辛,1996年,聚合物驱油技术在大庆推广,世界纪录随之诞生——中国成为首个实现化学驱三次采油大规模应用的国家;大庆石油采收率近70%,远超发达国家45%的水平。
王德民仍未止步,又率先向四次采油发起进攻。
“大庆石油含水量越来越高,采上来100吨液体,98吨都是水。”王德民解释,“我们开发出同井注采工艺,在井下油水分离,只采石油不采水,成本降幅巨大。”
又是十年呕心沥血。2020年底,同井注采顺利通过验收。王德民期待着它推广应用,“引发一场全球老油田复采的大变革”。
“你说,我能停下来吗”
耳濡目染间,一种热爱在传承。
王德民的儿子王研,是看着父亲伏案工作的背影长大的。那种专注,让他从小就对石油产生了兴趣。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大庆油田,一步步成长为采油二厂总工程师。
说起父亲,王研最大的感受只有一个字——严。“父亲不苟言笑,对工作、生活极严谨。我儿时难免抱怨,后来走上这条路,才理解他。”
科研是父子间最好的交流。同井注采,王研是项目负责人之一,年迈的父亲不再常到井边,但每天的电话雷打不动。“有时一打就是个把小时。小到一个零件的构造,大到整个系统的计算,都不容分毫偏差。”
这种严,王德民科研团队成员、东北石油大学教授马文国感受至深。
“王院士从不听‘左右’‘大概’。”马文国说,“一次路遇,他问:实验数据有什么变化?我说,‘和上次差不多。上次数据好像是,是……’院士脱口而出:‘6.51!你再测几次,认真分析。’我又佩服,又惭愧。”
王德民最严厉对待的人,是自己。
早年间,相貌堂堂的他却是出了名的“不修边幅”:常年一身工作服,脏了没工夫洗,也没几件可换;头发长得遮住了眼睛,也舍不得花时间理;常年熬夜伏案,鼻梁上架起厚厚的近视镜片。
后来工作愈发繁重,他恨不能“一分钟掰成两半用”。为省下烧开水冲泡的时间,索性干吃奶粉、咖啡粉充饥提神;不慎摔断腿,住院三天就回岗位;应酬交际极少参加,中午总是自带面包、水果在办公室吃,省下去食堂的时间……
“他算过,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7天,就是每天8小时、每周5天的2.1倍,相当于把为国家工作30年延长到60多年。”东北石油大学教授吴文祥回忆。
由于自小英语流畅、口才出众,王德民在新中国石油国际交流中被推到前台,荣获国际石油学会“三次采油先锋奖”等诸多奖项,也多次收到出国工作的邀请,而他“根本没动过这个念头”。“我的成就都是中国的。”他说,“正因为中国还不富裕,才更需要我。”
大庆,是王德民许下一生的地方。退休后,他本可以回到北京,回到从小长大的地方,与哥哥姐姐等亲人相伴终老。但他舍不得离开大庆,因为,“哪个城市有这么好的大油田,让我随时去研究?”
少年时代,王德民曾在北京市中学生短跑比赛中获奖。这位昔日的运动健将,如今把科研变成了一场没有终点的竞速跑,拼尽全力,也要跑赢油田的衰老速度。
“四次采油、绿色采油,还有一堆事情等着啊!”望着远处的油田,王德民问记者:“你说,我能停下来吗?”
 cription="编辑提供的本地文件" sourcename="本地文件"/>
cription="编辑提供的本地文件" sourcename="本地文件"/> cription="编辑提供的本地文件" sourcename="本地文件"/>
cription="编辑提供的本地文件" sourcename="本地文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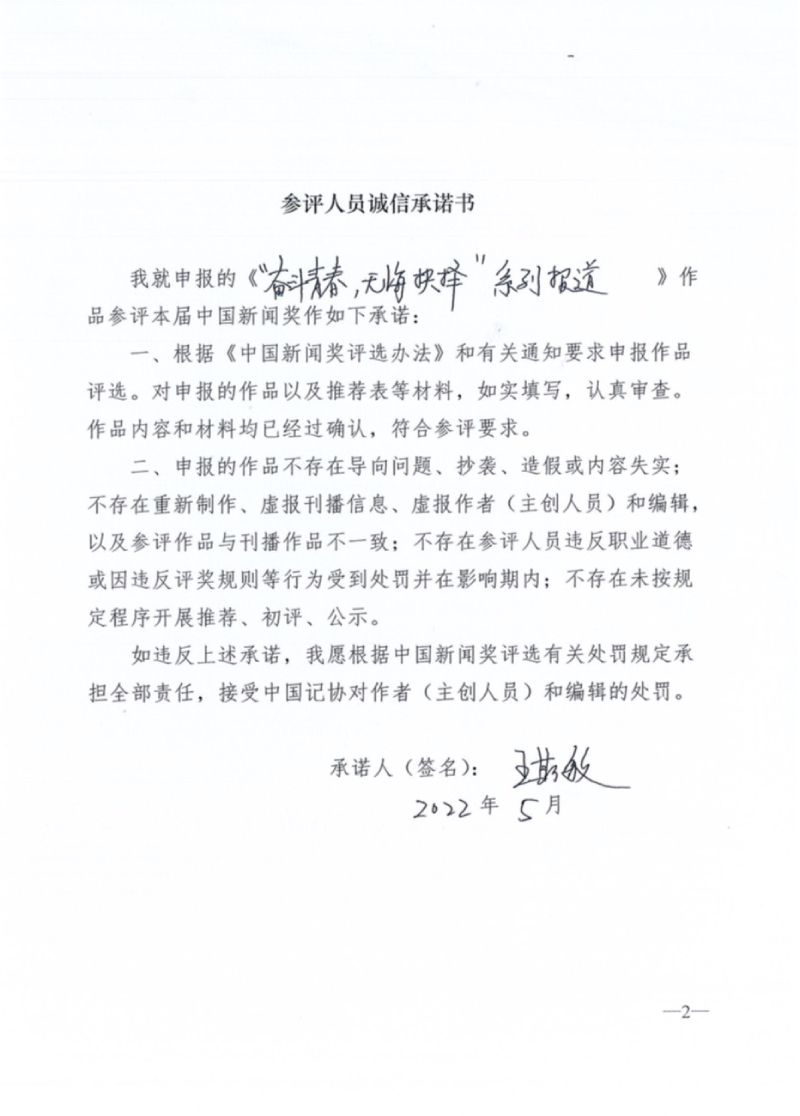 cription="编辑提供的本地文件" sourcename="本地文件"/>
cription="编辑提供的本地文件" sourcename="本地文件"/>